|
论文提要:诉讼欺诈是一种利用法院的审判权来实现不当目的的违法行为,不仅侵害了受害人的财权权益,也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目前学术界关于诉讼欺诈行为刑事定性的争议主要在于是否构成诈骗罪,因此对诈骗罪的解释是厘清诉讼欺诈行为定性的关键。通过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三角诈骗包含我国刑法上诈骗罪之中;但诉讼欺诈行为与一般的三角诈骗不同,也没有包含在“诈骗”的通常字面含义之中。从刑法解释的限度来看,刑法文本语词的可能字面含义是扩张解释与类推之间的界限。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确定“诈骗”一词的可能字面含义,而诉讼欺诈并没有突破“诈骗”的可能字面含义,因此将诉讼欺诈定性为诈骗罪不是类推,而是扩张解释。从刑法解释权限的分配来看,入罪的扩张解释应采用立法解释的形式较为恰当,因此可以通过立法解释形式将诉讼欺诈定性为诈骗罪。(全文共9975字)
关键词:诉讼欺诈;三角诈骗;刑法解释学;扩张解释
以下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诉讼欺诈行为定性之争
(一)现象与困惑:让司法不知所措的诉讼欺诈行为
诉讼欺诈是指诉讼欺诈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通过虚假陈述,利用伪造或变造的证据或使用其他不正当利用证据的手段,获得胜诉判决,从而使本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诉讼欺诈是恶意诉讼(1)的一种,诉讼欺诈的目的是为了使本人或者第三人获得财产或财产性利益,其行为的结果是造成对方当事人财产上的损失,而恶意诉讼的目的不限于谋取不正当利益,也可能单纯为了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恶意诉讼的结果可能造成对方当事人财产上的损失,也可能造成对方当事人人身和精神上的损害。
诉讼欺诈案件近些年来屡见不鲜,如“青岛市城阳区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诉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案”(2)、“杨义军等诉中铁二十二局劳动争议案”(3)。这些案件中诉讼欺诈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在手段上有的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的方式,有的采取隐瞒事实或变造证据的方式,在结果上有的行为人通过诉讼欺诈达到了目的,有的却自食苦果。司法机关对于诉讼欺诈的处理方式也各有不同。严重的诉讼欺诈行为不只是滥用诉权的问题,这种通过非法手段,利用司法的权威性来达到自己不当目的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仅仅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无法对受害人提供有效的保护和救济,必须通过刑事法律来加以调整。然而,诉讼欺诈问题在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上还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诉讼欺诈案件法律适用的困难,出现了性质相同的案件处理方式完全不同的现象,这是与罪刑法定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相违背的。
(二)争议与焦点:诉讼欺诈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
对于诉讼欺诈,与立法上的缺位和司法中的困惑相伴的是理论上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是诉讼欺诈的定性。从比较法上观察,德国与日本刑法理论界对此讨论较为激烈。与许多国家的刑法相同,德、日两国的刑法也没有将诉讼欺诈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不过两国的审判实践中有许多诉讼欺诈的案例是以诈骗罪处理的。(4)理论上,对诉讼欺诈是否构成诈骗罪,学者间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主张。多数学者在肯定三角诈骗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诉讼欺诈可以构成诈骗罪。国内学者们对于诉讼欺诈行为的性质的探讨,也大都是在讨论诉讼欺诈行为是否可以构成诈骗罪的基础上展开的。赞成者们一般采德、日学者多数说,在论证三角诈骗的基础上把诉讼欺诈定性为诈骗罪。反对者则坚持我国诈骗罪的传统理论,不赞成三角诈骗的观点,自然也就反对把诉讼欺诈定性为诈骗罪,并且在此基础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三)众说与关键:厘清争议必须对诈骗罪进行解释
关于诉讼欺诈的定性,目前学术界主要有诈骗罪说、妨害司法罪说、敲诈勒索罪说和无罪说等观点。妨害司法罪说认为诉讼欺诈行为侵害的两个客体即司法秩序和公私财物中,司法秩序是主要客体,公私财物是次要客体,因此诉讼欺诈行为应定性为妨害司法罪。但诉讼欺诈行为人实施诉讼欺诈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司法活动,而是为了欺骗法院以获取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侵犯他人财产是目的,破坏司法秩序是手段。目的引导、统帅手段,手段是为实现目的服务的。诉讼欺诈的本质就在于侵犯他人财产,而将其规定在“妨害司法罪”中的话,就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逻辑关系,误解了诉讼欺诈的行为本质。(5)对于敲诈勒索罪说,由于诉讼欺诈行为中并没有恐吓行为,也没有人因此产生恐惧心理,显然不能成立。而无罪说显然是在难以找到诉讼欺诈行为的准确定性情形下基于罪刑法定原则作出的无奈抉择。此外,关于诉讼欺诈行为定性最多数的观点就是诈骗罪说。对于诉讼欺诈是否构成诈骗罪,主要是基于对诈骗罪的不同解释而来证成或证伪的。(6)对于诈骗罪的不同解释,主要在于是否赞同三角诈骗的观点。由于很多成文法系国家刑法典关于诈骗罪的法条都用了简单罪状,因此需要对其加以解释。德、日刑法理论及审判实践均肯定诈骗罪中包含三角诈骗的情形,而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诈骗罪的特点是诈骗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使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而“自愿地”交付财产,如果被害人没有因被骗而交付财产,则不能算是诈骗。即认为诈骗罪只限于两者之间的诈骗。主张诈骗罪包括三角诈骗的学者认为诉讼欺诈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坚持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而不承认三角诈骗的学者认为诉讼欺诈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具有诈骗罪的特点,当然不能定性为诈骗罪。可见,对诈骗罪的不同解释是诉讼欺诈定性之争的关键。
二、以刑法解释方法对诉讼欺诈进行定性的前提——诈骗罪的解释
(一)刑法解释的基本方法及其与类推的界限
由于刑法文本的特殊性,对刑法的解释必须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必须遵循严格解释的宗旨。从解释的限度上看,刑法解释方法中的文义解释、扩张解释与类推之间必须严格把握。文义解释又叫平义解释,是严格按照法律文本语词通常的字面含义进行阐释和说明。平义解释又分为一般的平义解释法和特殊的平义解释法,一般的平义解释法是以“大众话语共识”解释刑法文本规定的日常用语的通常字面含义。特殊平义解释法则是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英话语共识”解释刑法文本规定的专业术语的通常字面含义。扩张解释是论理解释结果的一种。刑法的论理解释是指在解释特定刑法术语的语词含义时,在语词的通常字面含义之外而又不超越语词可能具有的含义的范围内,进行符合立法意图的阐释和说明。而延伸语词通常字面含义范围的解释就是扩张解释,与其相对应的是收缩语词通常字面含义范围的解释,即限制解释。(7)无论是刑法的文义解释还是扩张解释,都必须以刑法文本为基础,以所解释的文本所用语词可能具有的含义为界限。如果超越法律文本所用语词可能具有的含义,那就是类推了。
形式主义的罪刑法定原则禁止一切形式的刑法上的类推,现今主流的实质主义的罪刑法定原则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但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这样,刑法文本所用语词可能具有的含义就成了受限制的扩张解释和被禁止的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之间的界限,克劳斯·罗克辛教授称之为原文文字界限。罗克辛教授认为,解释与原文界限的关系绝对不是任意的,而是产生于法治原则的国家法和刑法的基础上。超越原文文本的刑法适用,就违背了在使用刑法力进行干涉时应当具有的国家自我约束,从而也就丧失了民主的合理性基础。(8)但是在具体的个案审理中,如何确定刑法文本所用语词可能具有的含义这个界限是个难解的谜。对于这个问题,想要抽象出一个一般的规则始终是很困难的,或许无法做到,只能在具体的案件中针对具体的刑法文本语词加以斟酌。
(二)三角诈骗是否属于诈骗罪——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的运用
我国刑法第266条对诈骗罪的罪状表述较为简单——诈骗公私财物,法条未对“诈骗”作任何具体的阐释,因此在对该法条的具体适用过程中,法官不可避免要对其进行解释。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诈骗罪的传统解释是: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9)并且一般认为诈骗罪限于两者间诈骗,其结构为: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行为人获得或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财产上的损害。对于诈骗罪的上述解释,体现了我国刑法文本“诈骗”这一语词的通常字面含义。三角诈骗的结构是否也属于“诈骗”的通常字面含义?也即把三角诈骗解释为诈骗罪的一种是否还是文义解释?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所谓三角诈骗,也就是受骗人(财产处分人)与被害人不是同一人(或不具有同一性)的诈骗。(10)三角诈骗的基本结构为: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财产处分人产生认识错误——财产处分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被害人(第三人)的财产——行为人获得或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财产上的损害。三角诈骗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甲委托乙代理出售一贵重物品,丙骗取乙先交货后付款,乙交货后丙销声匿迹。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看来,也会毫无疑问地会理解为诈骗。即从“大众话语共识”来看,受骗人处分的财产如果是第三人的并且其有权处分,那么即使财产受损害的是第三人,也不妨碍人们把这种情况理解为诈骗。现代社会财产关系复杂,财产的辅助占有比比皆是,财产辅助占有者受骗而处分财产所有人之财产的情况已是诈骗的当然意蕴。因此把三角诈骗解释为诈骗罪的一种是文义解释,而且是普通文义解释。
没有一个法律条文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必须作为整体刑法的部分要素来理解,这就需要运用刑法的体系解释来实现。体系解释,是指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把一项刑法条文或用语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放置于更大的系统内进行的,使得刑法条文或用语的含义、意义相协调的解释。(11)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诈骗罪也应当包含三角诈骗的情形。我国刑法上规定有票据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等特殊诈骗罪,这些诈骗罪与刑法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属于特殊法条与普通法条的竞合关系。除非有特别说明,一般来说,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同一语词在同一法律中应具有相同的含义。而票据诈骗中的“冒用他人汇票、本票、支票”的行为以及信用卡诈骗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均为三角诈骗的情形。这些特殊诈骗罪中的“诈骗”有包含三角诈骗的情形,根据体系解释的原则,对某一条文的语词不能从该条文本身得以理解时,可以求之于同一法律中其他条文中该语词的含义来理解,因此刑法266条所指的“诈骗”也应包含三角诈骗之义。
(三)诉讼欺诈是否包含在“诈骗”的可能含义之中——类推的排除
由于我国刑法对诈骗罪采用的是简单罪状,从条文来看,难以确定“诈骗”的可能字面含义,也难以确定诉讼欺诈是否有突破“诈骗”的可能字面含义。但从词源意义来看,诉讼欺诈应没有突破“诈骗”的可能字面含义。这一点可以从同为汉语刑法文本的台湾刑法和澳门刑法的规定中得到印证。台湾地区刑法第339条第1款对诈骗罪的规定是:“意图为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诈术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1000元以下罚金。”澳门刑法第211条第1款对诈骗罪的规定是:“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当得利,以诡计使人在某些事实方面产生错误或受欺骗,而令该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之财产有所损失之行为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从这两个规定表述的“诈骗”语词含义可看出,诈骗罪可能的含义所体现的该罪的结构是:诈术或诡计——受骗人受欺骗——受骗人本人或使有关第三人遭受财产损失。从该结构来看,诉讼欺诈并没有突破“诈骗”一词可能的含义。因此,将诉讼欺诈定性为诈骗罪并不是类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四)诉讼欺诈是否包含在“三角诈骗”的通常字面含义之中——扩张解释的提出
通过对诈骗罪进行解释,已经证明诈骗罪应当包括三角诈骗这种情形,那么诉讼欺诈是否包含在“三角诈骗”的通常含义之中,如果是,则将诉讼欺诈定性为诈骗罪就属文义解释,如果不是,则将诉讼欺诈定性为诈骗罪就属扩张解释。
1.诉讼欺诈中法官对被害人财产的处分权限或地位与一般三角诈骗不同
诉讼欺诈的结构为:行为人虚构事实、伪造证据提起民事诉讼(欺诈行为)——法官作出错误的判决——行为人基于错误的胜诉判决获得财产或财产性利益——被害人财产上的损害。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法官作出错误的判决是否是基于错误认识?二是法官对被害人的财产是否有处分权限?如果有,这种权限与三角诈骗中受骗人对被害人财产的处分权限或地位性质是否相同?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对于第二个问题,值得认真推敲。张明楷教授认为,在三角诈骗场合,受骗人(也即财产处分人)必须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地位,这种权限或地位可以是法律上的,也可以是事实上的。(12)从张明楷教授对三角诈骗的分析以及常见的三角诈骗来看,受骗人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如果是法律上的权限,那么这种权限一般是基于民商事的法律关系形成的,而且一般是在三角诈骗的实行行为发生前这种权限或地位已经存在。这种权限或地位一般是私法关系上的权利。如果受骗人的处分权限或地位是事实上的,那么其是否存在有两个判断标准,一是财产处分人有没有得到被害人的概括性授权,二是看财产处分人是否接近被害人的立场。一般来说,依据社会一般观念,如果财产处分人得到了被害人的概括性授权,则其具有事实上的处分权限或地位。而判断财产处分人是否得到了被害人的概括性授权又可以看财产处分人是否接近被害人的立场。(13)但是在诉讼欺诈中,法官处分被害人的财产的权限(也即通过判决书处分财产的权限)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力,这种权力虽然事先在法律上(比如宪法)有所规定,但在诉讼欺诈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实行之前这种权力是抽象的,只有在进入具体的诉讼关系后才变得具体,但这时诉讼欺诈的实行行为已经开始。所以,如果说法官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是一种法律上的权限,那这种权限的性质和形成的时间与一般三角诈骗中财产处分人的处分权限的性质和形成时间是不同的。法官的这种处分权限更不是事实上的处分权限,因为一来法官没有得到被害人的概括性授权,相反被害人是反对法官处分其财产的。二来法官也没有接近被害人的立场,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法官是中立的。
2.诉讼欺诈中被害人对欺诈行为的认识与一般三角诈骗不同
在常见的三角诈骗中,被害人对于财产处分人处分其财产的事实一般是不知情的,并且在一般的三角诈骗中,被害人对于财产处分人处分权限的形成起着主导作用,当其得知对其不利的诈骗事实时,能够利用这种主导作用进行有效干预。但是在诉讼欺诈的情形下,被害人对于法官作出的处分其财产的判决当然是知情的,并且也明白诉讼欺诈行为人的欺诈事实,只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服法官。这种情况下,被害人对于法官的权限形成当然不起主导作用,也就不能像一般的三角诈骗中那样进行有效的干预,从而有效地阻止欺诈发生。
3.诉讼欺诈被害人的救济途径与一般三角诈骗不同
在财产处分后,诉讼欺诈与一般的三角诈骗也是存在一些差别的。常见的三角诈骗,在受骗人处分了被害人的财产后,一般是难以回转的,只能通过刑事诉讼的程序来救济。但是在诉讼欺诈中,在法官作出的错误判决生效后(这时真正的财产处分才发生),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178条的规定,被害人还能申请再审,法院也可能主动通过再审程序纠正错误的判决。即使是在强制执行后,如果发现据以执行的判决有错误而纠正后,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4条的规定,仍可以通过执行回转程序追回财产。
4.结论——诉讼欺诈没有包含在“诈骗”的通常字面含义之中
通过分析可见,诉讼欺诈与一般的三角诈骗在财产处分方面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的,因此难以将诉讼欺诈说成是三角诈骗的通常形式。诉讼欺诈如果可以构成三角诈骗,也应当是一种十分特殊的三角诈骗。虽然从文义及体系解释角度看,我国刑法上的诈骗罪包括一般的三角诈骗情形,但诉讼欺诈与一般的三角诈骗有很多不同之处。因此,在我国刑法上,根据诈骗的通常字面含义理解,三角诈骗是包含在其中的,但是按照三角诈骗的通常字面含义来理解,诉讼欺诈难以包含在其中。因此,从刑法解释学来看,难以通过文义解释直接将诉讼欺诈定性为诈骗罪,而必须在诈骗罪的通常字面含义之外、可能字面含义之内通过扩张解释使诈骗罪涵盖诉讼欺诈。
三、以刑法解释方法对诉讼欺诈行为进行定性的途径——扩张解释的运用
(一)刑法扩张解释的可行性
刑法解释的限度问题一直以来是刑法解释理论上颇有争议的问题。在罪刑法定原则确立初期的启蒙时代,一些伟大的刑法思想家坚持形式主义的罪刑法定,反对刑法解释。在当代,主观(严格)解释论者主张刑法解释应当严格尊重和忠实于立法者通过刑法文本表现的立法意思,(14)反对超越这种立法意图的解释,超越刑法文本语词通常字面含义的扩张解释是不允许的。客观(自由)解释论者认为刑法解释不取决于当时立法者的意图,认为法律可能变化了的含义是最重要的,(15)因此超越刑法文本语词通常字面含义的扩张解释是允许的。折中解释论认为首先应当历史地解释法律,确定立法者的意思,只是在这种意思无法认知或对现代情势所生问题未提供解决基准的场合,才考虑在法律条文可能的语义范围内检讨可能的理由和基准,确认合乎现在法律适用目的的意义。(16)从折中解释论的立场看,扩张解释也是被允许的。
折中解释论的主张具有合理性,刑法解释应允许有限制的扩张解释。解释刑法首先应当探求在刑法文本中所表现的立法者当时的意图,这种立法者的意图是民意之体现。但是固定在刑法文本上的立法者当时的意图由于刑法的稳定性、修改程序的严格性难以适时改变,但是人民的意志和认识却在刑法文本之外变化着。如果机械地、刻板地忠实于立法者的原意,实质上是背离了人民的意志,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从微观角度讲,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和“所可能具有的最宽含义”往往是不一致的,前者的含义往往窄于后者的含义范围。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在个案中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是应当的,但是当个案发展为一种社会现象时,通过一种不溯及既往的扩张解释来为以后发生的个案提供处理依据,并不会违背罪刑法定的宗旨。在坚持最低限度的形式合理性的基础上,实质主义的罪刑法定(或称相对的罪刑法定)已成为现代刑法的主流。在刑法解释理论上,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扩张解释的合理性也得到了多数人的承认。因此,在刑法解释问题上允许一定程度的扩张解释(甚至是入罪的扩张解释)是有其民主宪政基础和解释学基础的,是被实践证明可行的。
(二)诉讼欺诈犯罪化的扩张解释之形式——立法解释的恰当性
法律是抽象的,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把抽象的法律与具体的事实相结合的过程,在逻辑上本身就蕴含着一个解释的过程。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解释是要严格按照刑法的字面含义进行的,个案中作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但是从实质的罪刑法定的角度看,如果严格按照刑法条文的通常字面含义得出的结论对于案件事实来说确实有违实质正义,不进行个案中的扩张解释就会违背刑法的精神与价值,那么就要看解释的主体是否被赋予了解释的权力。如果这法官或者最高审判机关都没有被赋予对刑法进行扩张解释的权力,那么就只能由立法机关在个案之外进行抽象的扩张解释,因为立法机关一般不会就个案进行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42条对我国的法律解释权作了规定:“法律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在这之前,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第1条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第2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综合相关规定来看: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最广泛的法律解释权,并且这种解释具有立法的效力,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无疑是拥有对刑法进行扩张解释的权力的。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可以分别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司法解释,从这一点来看,司法解释的目的在于保证现行法律的正确适用,因此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的内容为解释对象,一般不能进行扩张解释。另外,从以上这些规定并结合罪刑法定原则来看,至少在刑事案件中法官是没有对刑法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之权限的。因此,如果要对我国刑法上的诈骗罪作扩张解释而把诉讼欺诈这种行为包含进去,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解释的形式来实现。
(三)诉讼欺诈犯罪化的扩张解释之结论——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针对诉讼欺诈行为,一方面要通过扩张解释进一步明确诈骗罪的含义,另一方面要明确诉讼欺诈这种新的情况的法律适用依据,因此,针对诉讼欺诈行为进行的扩张解释的结论可以分两步进行:首先明确诈骗罪客观方面的结构: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财产处分人产生认识错误——财产处分人处分本人或者第三人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财产处分人本人或者第三人遭受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损失。这样,诈骗罪包含三角诈骗就有了明确的规定。其次,明确在诈骗罪客观方面的结构中,财产处分人的处分权限可以是通过民商法律关系形成的具体权利,也可以是法律直接规定的抽象权力;财产处分人的“具体”处分权限或地位的形成时间可以是欺诈行为实行之前,也可以是欺诈行为开始之后。这样,就把三角诈骗的含义由通常含义扩张到了最宽的可能含义,也就把诈骗罪的含义扩张到了最宽的可能含义。然后,对诉讼欺诈加以说明,明确诉讼欺诈客观方面的结构为: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法官产生认识错误——法官通过判决处分被害人的财产或财产性权益——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或财产性利益的丧失,进而明确可以把诉讼欺诈行为定性为诈骗罪。解释的结论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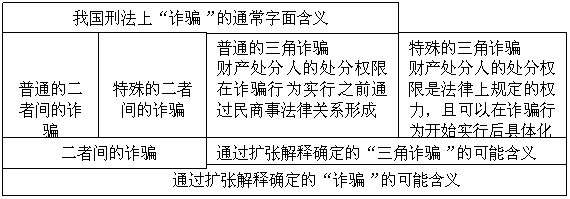
四、结语 法律是逻辑的,又是经验的。刑法解释不是盲目的,必须借助已有的经验为解释的对象寻找正确的逻辑基础和途径,排除那些偏离本质的观点之后,解释的道路才会导入正确的方向。关于诉讼欺诈定性的诸多观点只是“乱花渐语迷人眼”,从本质上看诉讼欺诈行为就是一种诈骗行为,但由于其特殊性,必须通过刑法解释才能达到逻辑证成。通过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寻找语词的通常字面含义与可能字面含义,为扩张解释与类推之间确定一个不能逾越的边界。在实质的罪刑法定原则成为主流后,刑法的扩张解释有其民主宪政和解释学基础,但在成文法系国家,刑法的扩张解释应选择立法解释才为恰当。对诉讼欺诈行为进行定性的过程也是运用刑法解释方法应对新的社会现象的逻辑演绎过程,这正是本文所要展现的。
(1)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虚构法律关系或主要法律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给相对人造成财产及精神方面损害的诉讼。参见张建权:《恶意诉讼问题探析》,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55页。
(2)雷文:《对一起诉讼诈骗案的两点思考》,载 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900/20/2005/4/
li929560441514500215390_165534.htm,于2012年5月27日访问。
(3)宋飞:《关于诉讼欺诈的案例分析及法律思考》,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法学院,2010年4月,第2页。
(4)张明楷:《论三角诈骗》,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99页。
(5)参见吴爽、陈源:《再论诉讼诈骗的概念和性质》,载《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59页。
(6)诉讼欺诈构成诈骗罪并不能用间接正犯理论来说明。虽然从形式上看诉讼欺诈过程中法官成了欺诈行为人的工具,但是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一般是被利用者实施的,间接正犯本人或欺骗、或胁迫、或设计圈套,让他人实施加害行为,但其并不直接完成加害行为,而诉讼欺诈的“欺诈”行为并不是法官实施的,而是欺诈行为人直接实施的,法院处分财产的行为并不是加害行为,因此如果诉讼欺诈行为构成诈骗罪,则欺诈行为人本身就是正犯。
(7)梁根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63页。
(8)德]克劳斯·罗辛克,《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88页。
(9)陈兴良:《陈兴良刑法教科书之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3页。
(10)张明楷:《论三角诈骗》,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99页。
(11)肖中华:《刑法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具体运用》,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5期,第17页。
(12)张明楷:《论三角诈骗》,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99页。
(13)张明楷:《论三角诈骗》,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99页。
(14)梁根林:《罪刑法定视域中的刑法解释论》,载梁根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15)[德]克劳斯·罗辛克:《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16)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195页。
|